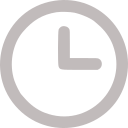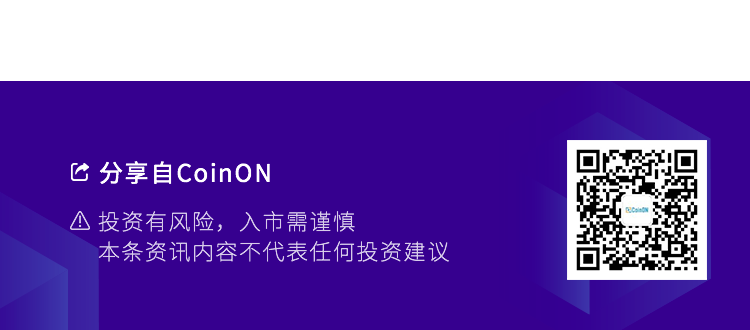翻译/校对:龙白滔
题注:本文为2019年12月3日欧洲央行执行委员会成员Benoît Cœuré先生在布鲁塞尔欧洲央行代表处的讲话。
我很高兴今晚欢迎你来到欧洲央行在布鲁塞尔的代表处。看到这么多长期的同伴和朋友,真是喜出望外。
该办事处成立于2011年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如今,布鲁塞尔办事处已成为欧洲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我们在当地的工作人员坚定承诺和奉献精神,这是我们对所有欧洲事务的关注和倾听。他们的网络对于我们从布鲁塞尔获得第一手洞察力和信息至关重要。
与我们主要的欧洲利益相关者保持高水平的合作和对话至关重要,我们不断努力进一步提高欧洲央行对欧洲议会和广大公众的透明度和问责制就是一个例证[1]。
但是,并非所有事情都掌握在我们手中。
多样性就是一个例子。考虑到我们的最新决定,自2012年年中以来,由于我们的多元化战略,ECB女性高级管理人员的比例从9%增加到31%。但是,所有19个国家的行长都是男性。这并不反映欧洲的现实。这损害了公众对我们机构和单一货币的信任。成员国应对这种情况负责。
该办公室的历史与我担任ECB执行委员会成员的任期历史正好吻合,我的任期即将结束。我于2012年1月加入ECB,就在办事处开业几个月后。
这是一个动荡的八年,很可能是欧洲战后历史上最具决定性的时期之一。这是一次信仰与斗争、尝试与错误的旅程。
事后看来,这场危机的部分代价反映了危机之前和期间所犯的政策错误,以及对我们的经济和货币联盟(EMU)设计缺陷的迟迟认识。我们有责任学习和做得更好。
但是我们也可以为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这些成就是显而易见、无可争议的。欧元区的失业率实际上已降至危机前的水平。工资正以十多年来最快的速度增长。调查显示,欧元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公众欢迎[2]。
这些成功并非偶然。需要作出重大努力来克服这场危机及其遗留问题。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遭受痛苦的人们。决策者们投入了巨大的政治资本,就国家和欧元区所需的改革达成共识,(这些改革)通过稳定与增长来恢复经济和社会福利。
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ECB已成功地保护了单一货币的完整性,克服了金融碎片化问题,使经济走上了复苏之路。
但是,有些伤口还没有愈合。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经济困难之后,欧元区的架构听起来可能令人不安,但它仍然无法抵御危机。
在公共债务高得令人无法接受的国家,经济增长周期性太弱以致无法完全恢复财政空间。银行的盈利能力仍然很低,在许多情况下,低于股本成本,反映出商业模式可持续性的风险[3]。
而生产力增长是支撑我们生活水平和社会安全网的主要组成部分,在许多成员国中仍然很低。因此,一些国家的失业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仍然高得令人无法接受,尽管在欧元区平均水平上取得了进展。
的确,许多其他发达经济体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但是,潜在的增长乏力和高债务的组合在一个具有分散的财政政策和金融市场整合不足的货币联盟中是有害的。
这意味着针对特定国家的冲击仍然是整个欧元区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它削弱了对进一步一体化的政治支持。这意味着面对不利冲击,单一货币政策必须承担宏观经济稳定的重担。
新的欧洲议会和委员会的到来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可以更加果断地解决剩余的漏洞,重新确定重点并相应地采取行动。它为我们提供了实现这些目标的时间表。
在今晚的讲话中,我将指出,我们既需要加强体制框架以使我们的货币联盟更具弹性,也需要实施正确的政策以提高我们经济的增长潜力。
我认为,灵活和富有活力的市场是欧元区的第一道防线[4]。它们是开启持续生产率增长的关键,从而使货币政策更快地正常化。它们还减少了对宏观经济稳定的需求,并遏制了有关危机管理的争议性辩论。
第二道防线涉及可持续和促进增长的财政政策。有财政空间的国家应该利用它来促进投资。债务高企的国家应调整其政策,以便在将来重新获得财政空间,从而限制他们对邻国带来的风险。所有国家都可以提高支出质量。
第三道防线涉及加强我们的共同工具包——涉及新的政策工具。如果冲击太大而无法被市场或国家财政政策吸收,则需要新的政策工具来保护货币联盟的稳定。新的政策工具还提供一个防止贫困和社会排斥的安全网。
第一道防线:整合和灵活的市场
在世界银行营商便利度指数的前十名中,没有一个欧元区国家。许多国家甚至没有进入前30名。
商业环境不那么友好的结果是欧洲的商业活力很弱。与美国相比,平均而言,欧洲国家“静态”公司所占份额较大,而成长中和萎缩中的公司所占份额较小[5]。
低商业活力助长并加剧了欧元区企业间资源的错误配置[6]。
经验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资本集中在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目前的错配率高于危机前任何时候[7]。
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的缺失,对创新和增长产生了压力。
大量证据表明,新公司更有可能采用新技术。企业进入率、技术创造和扩散、与生产力增长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8]。相对于就业份额,新公司和年轻公司也为创造就业做出了不成比例的贡献[9]。
疏通创新渠道要求我们改善市场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分配资源的方式。
在我看来,有三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
有效分配资源
首先,我们需要减少公司面临的进入壁垒,尤其是在服务行业,我们需要提高破产框架的质量。
一些欧元区国家缺乏早期私人债务重组的有效框架。例如,在葡萄牙、希腊和斯洛伐克,解决破产问题需要三年多的时间。在日本、挪威和加拿大不到一年的时间[10]。
缺乏有效的破产框架也使处理不良贷款变得更加困难。它限制了抵押品的执行,并增加了银行对“僵尸”公司宽容的风险[11]。
我们的经济治理框架——欧洲学期——有效地通报和交换了对我们经济的看法。
但是成员国没有说到做到。宏观经济失衡程序始终缺乏切入点,2018年针对欧元区国家的建议没有一项得到充分落实。
在这方面,国家生产力委员会是可以加强欧洲学期讨论的有益补充。
完善单一市场
其次,我们必须更好地利用单一市场提供的规模经济。
欧元推出20年后,我们面临着一个悖论。虽然单一货币最初被认为是对单一市场的补充,但在完成单一市场方面缺乏进展,现在这阻碍了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深化。
最初建立单一市场时考虑到商品的自由跨境贸易。但自那以后,我们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如今,服务业占欧洲就业的75%以上,而1970年是45%[12]。
随着增值和就业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作为增长引擎的单一市场日益失去吸引力。尽管有一揽子服务,但仍有5,000项国家法规保护各成员国提供不同类型的服务[13]。
这些障碍阻碍了欧洲服务公司实现规模和盈利。结果,尽管经济体的规模大致与美国相似,但欧盟的服务公司数量却是美国的三倍[14]。
碎片化使竞争缺失长期存在,并阻碍了围绕效率最高的公司的健康整合。大型公司通常更多投资于人力资本和品牌资本以及无形资产,如知识产权、软件和数据库[15]。它们也比小公司更有可能出口。
因此,完善单一市场,特别是针对服务业,是我们努力提振疲软的生产力增长的核心支柱。
这将使我们的货币联盟更具弹性,并支持实际利率正常化朝更高、更积极的水平迈进。
成立资本市场联盟
第三,如果公司要扩张和成长,我们需要扩大和深化可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金组合[16]。
欧元区的公司主要依靠银行贷款为其债务融资。
这引起了两个广泛的关注。
首先是欧元区80%以上的银行贷款仍然是国内贷款[17]。这限制了对良好信用的竞争,并加剧了主权信用和银行信用之间的恶性循环,我们未能根除这种恶性循环。
其次,银行常常不愿为抵押品价值难以量化的无形资产提供资金,或为未来付款流高度不确定的新型可持续技术提供资金。
欧洲央行的最新研究表明,在将投资重新分配给“绿色”部门方面,股票市场比银行更好,并且在股票市场较深的国家中,有形资产较少的创新部门增长更快[18]。
但是,在欧元区,股票市值(不足美国的五分之一)太低,无法以这种方式充当催化剂。跨境一体化程度同样较低[19]。
我们的资本市场必须变得更深,同时,对于初创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来说,必须更容易进入。
实现真正的一体化资本市场是面对巨大的全球挑战(例如气候变化或数字化)时找到所需的集体对策的唯一方法。
迫切需要资本市场联盟的另一个原因是,资本市场有助于各国更好地分担经济风险。
例如,在美国,对一个州的GDP的冲击有70%是由金融市场缓冲的,而在欧元区,这一比例接近20%。资本市场联盟可以极大地帮助分散并降低风险。
当然,如果认为不投资政治资本就可以实现资本市场联盟,那就太天真了。例如,改进和协调国家破产法是我们法律制度的核心。但这是良好投资的(政治)资本。
私人投资者的风险分担减少了公共风险分担的必要性,也减少了经常随之而来的旷日持久和激烈讨论的必要性。
没有欧洲层面对系统性中介机构和基础设施的监管,资本市场联盟就无法运作。
有大量的跨境溢出效应,如果出现问题,由欧洲央行直接监管的银行将承担大部分金融风险。欧洲监管机构、欧洲市场和基础设施法规(EMIR)最新的改革错失了机会。
英国脱离欧盟将对欧洲金融市场的架构产生持久影响。这加强了应对和完成资本市场联盟的必要性。
第二道防线:健全的国家财政政策
国家财政政策在货币联盟中扮演着两个关键角色。
首先是支持融合、增长和资源的有效分配。
但是,在许多欧元区国家,特别是针对低收入者和次要收入者的劳动税楔子[1]仍然过高,抑制了劳动力的供求。
通过将税收从劳动力转移到环境外部性或财产上,许多欧元区国家有空间以税收中性的方式减少其税收体系的扭曲影响[20]。
这种国家努力应辅以更紧密的税收合作。在欧盟一级商定并执行资本收入的最低税率,将有助于各国重新获得减少劳动所得税的空间,从而促进就业增长。
支持增长还意味着更加明智地支出。
欧元区的公共投资从2009年的GDP的3.7%下降到2018年的2.7%。与此同时,包括学校、医院和道路在内的大部分公共基础设施都迫切需要维修和现代化。
当前的利率环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可以通过动员投资来支持数字化并加速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从而缩小公共投资差距并增强欧洲的创新能力。
这也需要审查和增加无形资产的支出。
在过去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欧盟用于研发(R&D)的支出一直停滞在GDP的2%左右。在最大的欧元区国家中,用于研发、教育和运输的公共支出约占基本总支出的15%或更少[21]。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与环境有关的公共研发支出仅占经合组织国家研发支出总额的1.6%。鉴于市场在环境研发方面的投入不足,而且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因此公共部门迫切需要介入。
财政政策在货币联盟中的第二个作用与稳定和弹性有关。
在这两个方面,《稳定与增长公约》基本上都失败了。
事实证明这并不管用。在繁荣时期,建立足够的财政缓冲以应对经济衰退的必要性被忽略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它会放大顺周期性。从2009年到2018年,经周期性调整的政府一级资本平均余额,日本为-5.7%,美国为-3.6%,而欧元区为0.5%。
而且,即使在最近几年,欧元区的总体财政立场被大体认为是适当的,它在各个国家之间的分配也是错误的。有财政空间的国家没有使用它,没有财政空间的国家正在尝试发明一些[22]。
结果,从字面上看,货币政策必须弥补这一懈怠。
在没有真实的反事实的情况下,容易做出假设。但是我相当相信,如果各国政府能够更有效地执行欧洲学期的建议,欧洲央行近年来为稳定欧元区经济而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措施,以及使之(措施)成为某些成员国批评的目标,是可以避免的。
《稳定与增长公约》日益复杂化及其执行的政治化并没有很好地为我们服务。
因此,我们需要审查规则及其执行情况。我们需要简化它们,使其非政治化并提高国家所有权[23]。各国政府不应再选择利用漏洞或指责布鲁塞尔的技术官僚来掩饰其责任。
各国政府对选民负责。强大而独立的国家财政委员会应向公众清楚地说明轻率的财政行为对国家和整个欧元区稳定的潜在后果。不幸的是,我们不再缺少例子。
第三道防线:有效的区域性工具
危机表明,系统性冲击可能超出国家财政预算提供的有效稳定的能力。
欧洲稳定机制(ESM)在运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是一种危机管理工具,其本身的作用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因为做出了受欢迎的决定使ESM成为单一解决基金的后盾并引进了新的预防措施。
但是,ESM应该能够通过以合格多数决定来在危机中采取果断行动,并且应该根据共同体法律对欧洲人民负责——这两项目标在当前改革提案中没有涉及。
让我再说一遍:政府间的决策在短期内在政治上可能是方便的,但从长远来看会带来很高的经济成本。它有利于拖延,把每个决定都变成零和游戏。
政府间危机管理增加了危机的代价,就调整负担而言,对希腊人民而言,对希腊债权人而言,对风险敞口和潜在损失而言,对整个欧洲而言,对信任和统一而言,对整个欧洲而言,都是如此。这不是前进的道路。如果我们不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教训,我们将责怪自己重蹈覆辙。
这就是为什么目前的提议只能是第一步。我们缺少的是三个相辅相成的工具。
共同的欧洲存款保险计划
首先是共同的欧洲存款保险计划,这是真正的一体化银行体系和单一货币的先决条件。我欢迎目前在就这一计划进行政治谈判方面取得的进展。
应该在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向上并行取得进展。首先,通过激励银行以不干扰政府债券市场运作的方式分散其主权敞口,消除银行—主权的厄运循环。
第二,加强我们的解决框架。如今,只有少数几家银行被认为符合公众利益,并受制于欧洲解决方案,因此大多数银行倒闭都可以通过十九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这是站不住脚的。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为银行清算创建单一的管理工具将是重要的第一步。
共同的财政能力
第二个缺失的工具是共同的财政能力,它提供了宏观经济稳定,以防止或减轻系统性冲击——也就是说,在冲击变成全面危机之前。
当前正在实施的预算工具有一个不同的目标,即提高竞争力和趋同,这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目标,尽管现有工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一问题。但它并非旨在提供宏观经济稳定。即使是这样,它也不足以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我们还艰难地认识到,协调国家的财政政策不会导致整个欧元区采取适当的财政立场。当前经济增长乏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即使政府加强了协调,跨境溢出也可能太小而无法发挥作用。例如,欧洲央行的研究表明,跨境溢出可能不到初始支出的10%[24]。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欧元区需要共同的财政工具。这样的工具将支持货币政策,并防止在经济不景气时出现顺周期紧缩政策。这将增强人们对国家自动稳定器的信心,从而保护就业并最大程度地减少产出损失。
所有成功且稳定的货币联盟都拥有真正的财政工具,这些工具建立在强大的法律和市场化的机制之上,确保国家一级的财政纪律。这种工具不应取代国家政策,但必须足够大以有效地补充它们。
共同的安全资产
全球治理面临威胁[27];为加深和整合我们的资本市场做出了巨大努力。
结论
在欧元区危机及其直接后果的胁迫下,我们在使我们的货币联盟更适合目标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我们可以为过去的成就感到自豪,但今天的步骤更加不确定。当太阳照耀时,欧洲将再次无法修缮其屋顶。这种风险很高。
Jean Monnet著名的预言“欧洲将在危机中锻造,并将成为针对这些危机的解决方案的总和”,这可能再次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要付出什么代价呢?现在,当前的讨论倾向于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的循序渐进的方法。
但是在我们这个不确定的时代,采用这种渐进式方法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永远无法到达河的对岸,并且有被河流带走的风险。
我相信,新的欧洲领导层将找到给欧元区新方向和新步伐的决心,并为欧洲央行提供维持我们的单一货币健全和稳定所需的环境。
谢谢!
[1]SeeCœuré, B. (2017), “Independence and accountability in a changing world”,introductory remarks at th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EU Event “Two sides ofthe same coin? Independence and accountability of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Brussels, 28 March.
[2]See2019 Standard Eurobarometer.
[3]See ECBBanking Supervision (2019), “Risk assessment for 2020”, 7 October.
[4]For anearlier contribution, see Cœuré, B. (2018), “The euro area’s three lines ofdefence”, speech at the conference “Deepening of EMU”, Ljubljana, 2 February.
[5]SeeBravo-Biosca, A. (2017), “Firm growth dynamics and productivity in Europe”,in Remaking Europe: the new manufacturing as an engine for growth,Bruegel.
[6]SeeCœuré, B. (2017), “Convergence matters for monetary policy”, speech at theCompetitiveness Research Network (CompNet) conference>
[7]Ibid
[8]See,for example, Anderton, R., Di Lupidio, B. and Jarmulska, B. (2019), “ProductMarket Regulation, Business Churning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theEuropean Union Countries”, ECB Working Paper No 2332. See also Canton, E.(2016), “Drivers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EU: the role offirm entry and exit”, Quarterly Report>
[9]SeeCalvino, F., Criscuolo, C. and Menon, C. (2016), “No country for young firms?Startup dynamics and national policies”,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PolicyPapers, No 29, OECD Science.
[10]SeeConsolo, A., Malfa, F. and Perluigi, B. (2018), “Insolvency frameworks andprivate deb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ECB Working Paper No 2189.
[11]SeeAndrews, D. and Petroulakis, F. (2019), “Breaking the shackles: Zombie firms,weak banks and depressed restructuring in Europe”, ECB Working Paper No 2240.
[12]SeeCœuré, B. (2019), “The rise of services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policy”, speech at the 21st Geneva Conference>
[13]SeeEconomist (2019), “Briefing: The economic policy at the heart of Europe iscreaking”, 12 September.
[14]Ibid.
[15]See, forexample, Crouzet, N. and Eberly, J. (2018), “Intangibles, Investment, andEfficiency”, AEA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08:426-31. In Italy, for example, approximately three-quarters of the productivitygap to the global frontier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fact that national frontierfirms – while actually quite productive in global terms – are relatively smallcompared with those at the global frontier. See Andrews, D. and Cingano, F.(2014), “Public Policy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Evidence from Firms in OECDCountries”, Economic Policy, Vol. 29 (78), pp.253-96,
[16]Seealso Cœuré, B. (2019), “European capital markets: priorities and challenges”,dinner remarks at the International Swaps and Derivatives Association,Frankfurt am Main, 25 June.
[17]Despitesignificant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to develop a more coherent policyframework for cross-border banking, namely with the single rulebook and thecreation of European supervision and resolution.
[18]See DeHaas, R. and Popov, A. (2019), “Finance and Carbon Emissions”, ECB WorkingPaper No 2318.
[19]Just20% of euro area equity holdings are issued in other euro area countries. Forbonds, the share is 30%.
[20]See,for example, European Commission Directorate General Economic and FinancialAffairs (2017), “Financing labour tax wedge cuts”, technical services note tothe Eurogroup.
[21]SeeEuropean Fiscal Board (2019), Assessment of EU fiscal rules, with a focus>
[22]See the2019 Annual Report of the European Fiscal Board.
[23]Forproposals, see, for example, European Fiscal Board (2019, op. cit.); Eyraud, L. and Wu, T. (2015), “Playing bythe Rules: Reforming Fiscal Governance in Europe”, IMF Working Paper 15/67; andDarvas, Z., Martin, P. and Ragot, X. (2018), “European fiscal rules need amajor overhaul”, Bruegel Policy Contribution, Issue18, October.
[24]SeeAlloza, M. et al. (2019), “Fiscal spillovers in a monetary union”, Economic Bulletin, Issue 1, ECB.
[25]For anoverview, see Giudice, G., de Manuel Aramendía, M., Kontolemis, Z. andMonteiro, D. P. (2019), “A European safe asset to complement nationalgovernment bonds,” MPRA Paper 95748,University Library of Munich, Germany.
[26]Alternatively,this could be achieved by lifting the zero risk weight that government bondscurrently enjoy under the prevailing regulatory framework.
[27]SeeCœuré, B. (2019), “The euro’s global role in a changing world: a monetarypolicy perspective”, speech at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ity,15 February.
>>>点击进入「 龙白滔博士必读系列文章」专题<<<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